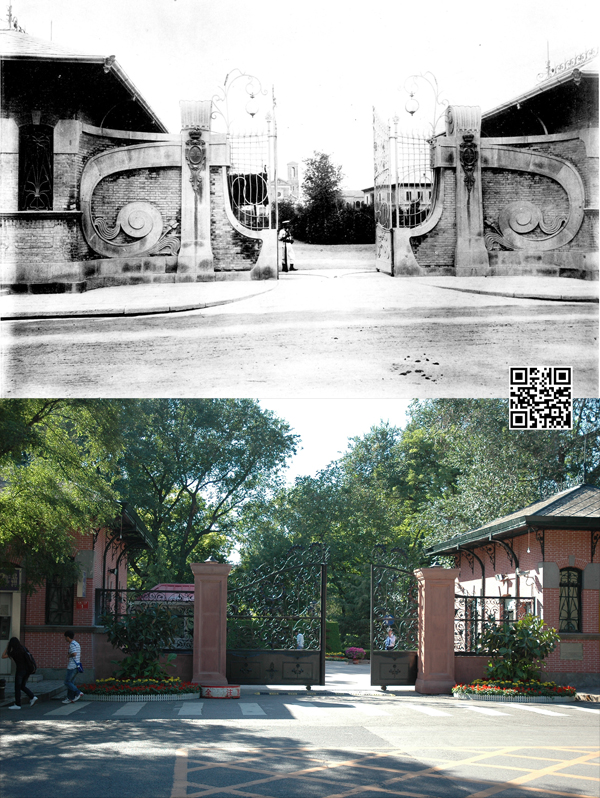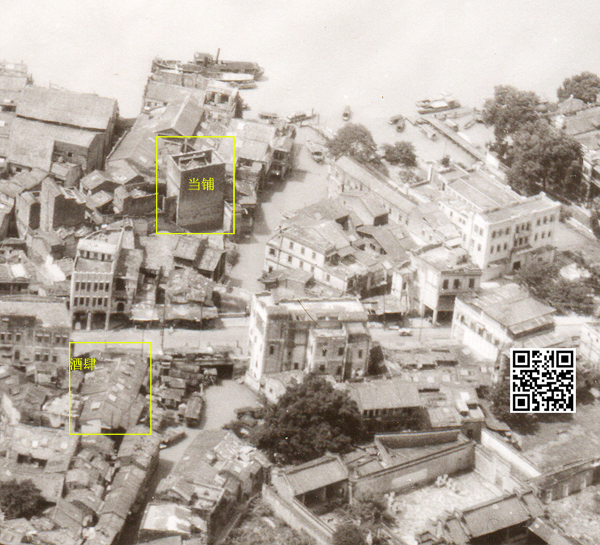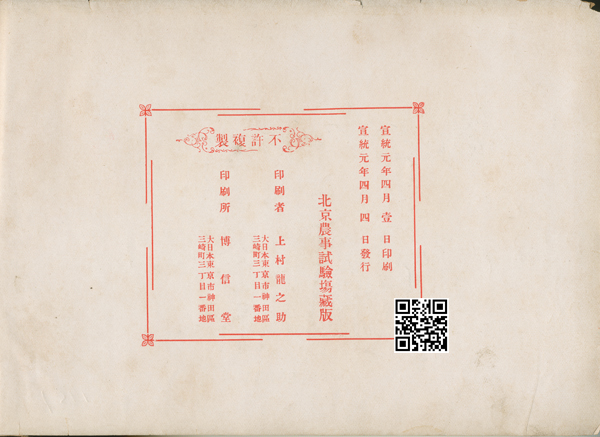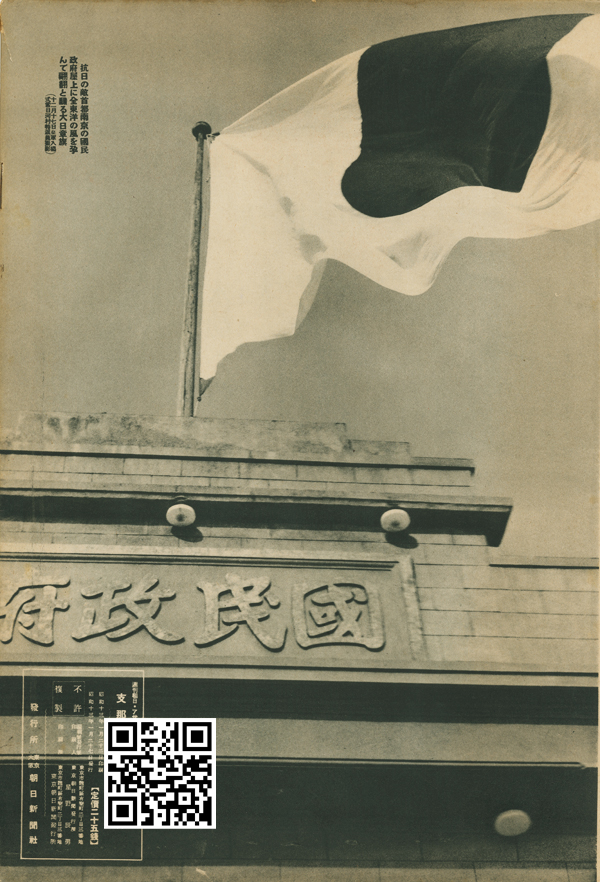现存有关中国的立体照片中,发行量最大,流传最广的就是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拍摄,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1901年发行的《China: Through the Stereoscope》。关于这套照片到底有多少个版本,同一个场景拍了几张照片直到今天都是一个疑问,我也在Blog里连着写了好几篇《立体照片找不同》,就是把不同的版本放在一起比较。基本上,同一个场景至少拍两张(至少从发行的情况来看是这样的),而我最近发现利大爷在1900年9月27日于天津的总督衙门拜见李鸿章时至少拍了四张照片,也就是U & U公司发行的那套立体照片中至少有四个版本的李鸿章!
 这张是最常见的版本,中堂大人的形象也最好,既威严又和蔼,很符合当时义和团运动下外国人期望的中国官员形象
这张是最常见的版本,中堂大人的形象也最好,既威严又和蔼,很符合当时义和团运动下外国人期望的中国官员形象
 多了个仆人的形象,削弱了照片的主体,而且光着头,明显不是那么威严了,显得老态
多了个仆人的形象,削弱了照片的主体,而且光着头,明显不是那么威严了,显得老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