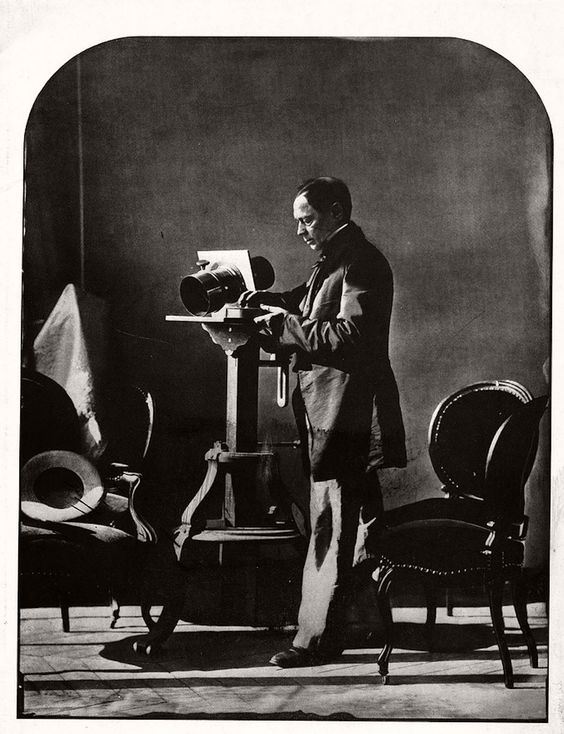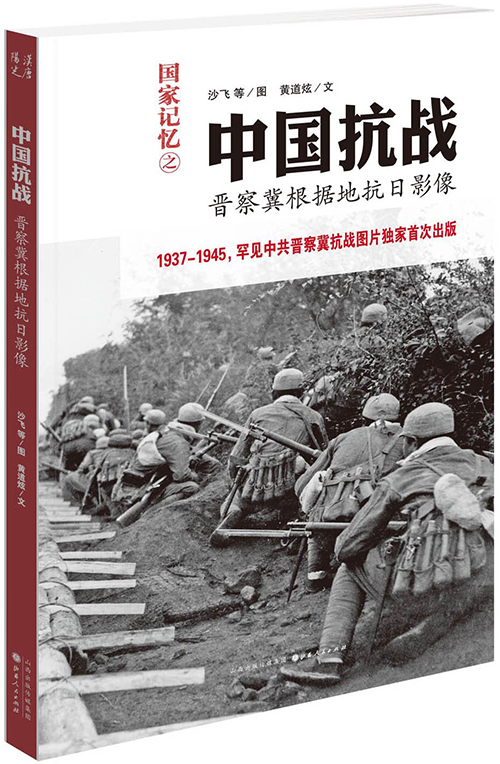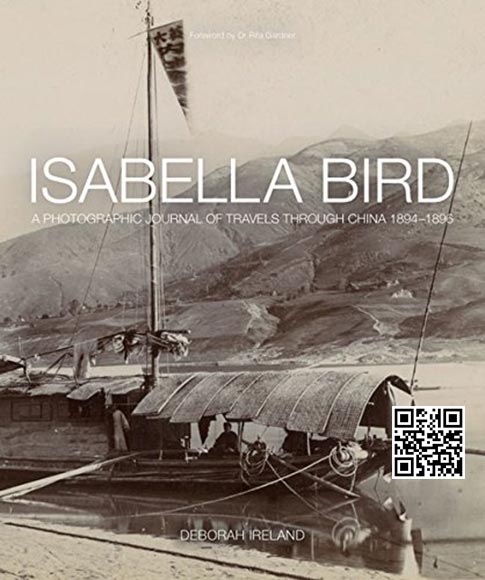开始这篇前先说几句无聊的话。
很久没有更新了,既对不住自己,也对不住仍然关注网络上这么一小块空间的朋友们。2016年第一天到来前的几个小时,手里的事情终于忙的只剩一件(尽管我希望所有的项目都能得到了结,但是影响进度的因素往往不是我能掌控的),算是有了一点时间。其实在没有更新的这段日子里,我仍然保持每天的照片“阅读”量,积攒了些可以写下来的题目,2015年已经离去,2016年已经到来,这第一篇就从“背影”的话题开始。
之所以想说背影,是因为前段时间在一场国外的照片拍卖会上看到一张法国著名摄影师爱德华·布巴(Édouard Boubat, 1923-1999)的作品,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在房顶上,面对繁华的城市,旁若无人的神情拥吻。当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大脑下意识的检索了遍图片库,匹配出一张老蒋和宋美龄的合影,那是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老蒋夫妇在罗伯特·格里格爵士(Sir Rober Greg)的陪同下参观开罗的穆罕穆德·阿里清真寺,在最高的平台俯瞰整个开罗老城,蒋宋两人虽然没有拥吻,但是全程都手牵着手,鹣鲽情深,和布巴那张照片的氛围相合。

布巴拍摄的那张在楼上拥吻的青年男女

蒋宋二人手牵着手听罗伯特爵士介绍开罗老城
于是,我又想到一张老蒋背影的照片,那是在蒋宋这张合影的6年后,1949年1月22日,老蒋来到溪口老家短暂逗留,当他和蒋经国在山上俯瞰家乡的时候,摄影师悄悄拍下一张二人的背影,最后众所周知,老蒋自此离别故乡,至死未回。

蒋介石(左)和蒋经国(右)在山上俯瞰家乡,他心里在想什么谁又能知?
宋美龄也有一张背影照片,可比上面这张老蒋的开心多了。1943年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受到热烈欢迎,当地政府组织的欢迎仪式规模也一个赛一个,旧金山的华人人口多,华侨们为欢迎宋美龄组织了人数庞大的游行,宋美龄是站在市政厅的阳台上观看游行的,摄影师为她拍下一张背影照片,看得见下边道路上漂亮的花车和黑压压的人群。

宋美龄访问旧金山时观看为她组织的游行
对于摄影创作,拍摄普通人的背影很正常,早在还没有摄影术的绘画时代就流行画裸女大屁股的背影呢,这没什么稀奇。摄影被用作新闻报道,摄影师拍摄的视角就是观众观看的视角,因此对于伟人和领袖,不拍摄看不见脸只看见后脑勺的背影似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但是,偶尔打破一下规矩似乎会有更好的效果。如果只拍伟人和领袖的正面,尽管可以通过仰拍表现其高大,可以通过面部特写表现其内心,可以通过不断出现的面孔实现“洗脑”(加深印象),但毕竟还是会缺乏一些信息。比如,朝鲜金三胖的报道,正面和侧面很多,总是笑眯眯拍手,总是有一堆人拿着小本本跟着他,但是作为观众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为什么而笑而鼓掌,除非有别的镜头补充,才能知道他是在视察养鱼场还是接见痛哭流涕的民众。如果拍摄伟人和领袖在一个场景里的背影,反正他们大家都认识了,已经成为符号,不需要被仔细观看,就可以通过画面向观众传达被摄对象正在观看的内容,这些被观看的内容则可以反过来衬托被摄对象,达到特定的宣传效果。
伟人和领袖这样的背影照片,我马上能想到希特勒的两张,一张是1933年的多特蒙德,元首站在主席台上向纳粹党员们发表演说,巨大的广场上站满了人,一队一队排列着,似乎望不到头,远处是飘扬着的纳粹党旗。这张照片传达的信息就是团结和集中,体现元首的地位。当然,用正确的立场来说就是极权。

1933年希特勒在多特蒙德发表演说
还有一张是1940年6月巴黎被践踏在德军的铁蹄之下,希特勒和他的随从访问了巴黎,在他观看埃弗尔铁塔时,摄影师从他背后拍摄了一张照片。埃弗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当元首一身军装的身影出现在塔前的时候,说明这座城市沦陷了,这张照片传达的信息就是纳粹德国对法国的征服和占领。

1940年,元首望着埃弗尔铁塔,不知他是否感到心满意足?
说到伟人和领袖的背影照片,还有一张不得不提,就是1957年11月17日,毛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大学礼堂接见了留苏学生代表,那句著名的“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就是毛在那次接见时说的。摄影师侯波也很例外的在毛讲话时拍了一张他的背影。当然,这张照片观看的不是毛,而是主席台上主席台下盯着毛的一双双眼睛,这种被观看的观看,可以解读为对领袖的热爱和敬仰,我想这也是摄影师当时想传达给观众的。

1957年毛在莫斯科大学礼堂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