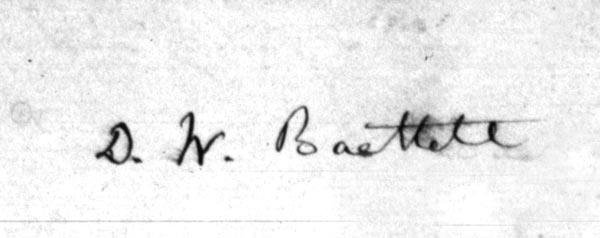去一个未曾踏足过的地方,有当地的人襄助,肯定会省却很多烦恼。国与国之间的外交也是这样,雇佣当地人是传统,外国驻华使馆会雇佣中国员工,中国驻外使馆也会雇佣当地员工。晚清时候中国政府雇佣的洋员挺多的,其中比较有名的比如洋枪队的华尔、福建船政局的日意格等,大都集中在军事、工业、语言培训等方面,外交口大家都知道蒲安臣,实际上大清国第一任驻美使馆就曾雇佣了一位英文秘书,洋员柏立。驻美国公使馆的洋员应该具备了解美国风俗、熟悉美国政界、得体可靠的素质,柏立又是如何被选中的呢?学界似乎少有人关注柏立,鲜有他的资料,我根据能找到的史料简单梳理一下。
清政府最初对设立驻外使馆是排斥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始有外国使馆驻扎北京,按照对等条约,清政府也应该向这些已经有驻华使馆的国家派驻公使,但迟至1875年“马嘉理事件”后,郭嵩焘才因赴英国道歉而成为大清国第一位驻外公使。向美国派驻公使,则是因为在古巴(当时是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的殖民地,即后文之“日国”)和秘鲁都发生虐待华工的事件,为此总理衙门上书说“臣等参考各国情形,必须照约于各国就地设领事等官,方能保护华工,既欲设领事等官,必先简派大臣,出使彼国,方能呼应。古巴境地暨秘鲁国之地,均与美国相近,秘鲁凌虐华工情事,曾经美国使臣据词代向臣等申诉,其对于日国招工事件,亦持公论。且近年奏选学生出洋肆习西学,所驻哈富,即系美国境地,亦有交涉应办之件。此事欲遣使日国、秘国必先遣使美国,方能取程前进,逐层开办,是美国及日国、秘鲁遣使一层,均难稍缓,而三国同时遣使不易骤得多人,似以请派使臣二员,合办三国事宜为较便。”于是,同时兼任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公使就成了清政府的传统,一直持续到民国肇建。大清国的外交人才捉襟见肘,总理衙门说“熟谙美日秘等国情事者惟陈兰彬一员”,说他熟谙,是因为陈兰彬是第一任留美幼童监督,并曾亲赴古巴考察华工被虐情事。身兼三国公使,一个人肯定是干不来的,于是总理衙门又推荐了留美幼童副监督,三品衔同知容闳作副使,他不仅“熟于洋语洋律办事奋勉”,而且曾奉命前往秘鲁考察华工被虐情事。陈兰彬到美国后发现“交涉事几于无日无之,臣等呈递国书后应即知照该外部派设中国领事,妥为保护将来美都使署一切事务亦必纷繁”,自己又“不日仍须前赴日国秘国”,于是“商酌必须在此添用人员常驻料理”,他推荐了已经在美国七年的留美学生监督五品衔花翎保升主事容增祥为参赞,“并用美国人柏立一员帮同照料”。这是陈兰彬在光绪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上的折子,实际上他是先斩后奏,据他自己的日记,光绪四年九月初三日去白宫向美总统呈递国书的时候就提到洋员柏立,“巳正三刻,兰彬与副使闳率同参赞容增祥,翻译陈善言、蔡锡勇,俱用行装,并洋员柏立,乘马车先到外部衙门……”
柏立(David W. Bartlett, 1828年4月16日-1912年6月25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文顿伯里(Wintonbury),这个拗口的拼写源自其周边三个小镇名称,温莎(Winsor)、法明顿(Farmington)和希姆斯伯里(Simsbury)各取一部分的组合。1835年5月,文顿伯里合并到布鲁姆菲尔德(Bloomfield)直到现在。柏立的父亲是当地一位受尊敬的牧师约翰·巴特里特(Rev. John Bartlett),1866年病逝于东阿旺(East Avon),他的母亲珍(Jane)是沃伦镇(Warren)法官大卫·戈登(David Golden)的女儿。用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名字组合成新生儿的名字在欧美国家是种传统,比如柏立父亲的名字“John”就源自他奶奶(Deacon John)家的姓,柏立名字中的“David”可能是源自他外祖父的名字。不过很遗憾,我没能查到柏立中间名的“W”全称是什么,无论是他在文件上的签名,或是他墓碑上的刻字,中间名都只有一个孤零零的“W”,不禁让我开脑洞:要么是他真的非常不喜欢这个中间名,要么他的中间名就是只有一个字母“W”!
柏立给美外交部函件上的签名
不清楚柏立早年的教育情况,但是他应该花了很多时间在欧洲游历,并密集地出版了几本著作,比如《伦敦见闻》(What I saw in London, 1852)、《简·格雷女士的生活》(Life of Lady Jane Grey, 1853)、《煽动者的肖像》(Pen-Portraits of Modern Agitators, 1855)、《笔下的巴黎》(Paris with Pen and Pencil, 1858)。柏立不仅写书,还长期担任纽约《独立报》(Independent)、《晚报》(Evening Post)和春田市《共和报》(Republican)的通讯记者,并在186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林肯的传记(The life and public services of Hon. Abraham Lincoln, 1860))。从这段经历看得出来,柏立的文笔应该不错,对欧洲有一定了解,对美国的媒体业很熟悉。大概在1865年左右,柏立成为美国众议院选举委员会的书记员,并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几年,这样的经历让他近距离接触了美国的政治圈,熟悉了当时美国的政治生态,也积累了一定的人脉。柏立之前的这些工作经历和人脉资源都使他成为适合为中国服务的人选,当清政府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他被聘为大清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英文秘书。
柏立又是如何与新到美国的中国公使团建立联系的呢?实际上这里边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在陈兰彬和容闳的带领下,第一批共30名留美幼童抵达美国,最后落脚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为了让这批幼童能尽快进入学习状态并感受家庭的温暖,他们被分为3-5人一组入住当地人家庭,在这批幼童抵达康州的时候,已经有122个家庭表达了愿意接收幼童的意愿,其中接收蔡绍基、吴仰曾、梁敦彦和黄开甲四人的是大卫·巴特利特家。不过这个大卫·巴特利特不是柏立的那个“大卫·巴特利特”,他的中间名是“E”,是柏立的堂弟。也就是说在陈兰彬和容闳,这两位后来大清国驻美国的正、副公使在1872年初抵美国时就已经认识了柏立家。1873年第二批幼童中的张祥和与1874年第三批幼童中的康庚龄、沈嘉树都入住在威廉·凯罗克(William H. Kellogg)家,威廉同时兼任出洋肆业局的英文秘书。1874年容闳与威廉的姐姐玛丽(Mary Kellogg)结识,两人一见钟情,并在次年结婚。尽管相差24岁,但是容闳夫妇非常恩爱,他们婚后育有两个儿子。巴特利特家和凯罗克家关系很近,柏立的父亲和玛丽的祖父贝拉牧师(Rev. Bela Kellogg)都服务于东阿旺的教堂,而且柏立是玛丽的舅舅。1886年6月28日玛丽因肾病不幸去世。容闳对妻子娘家人都很好,据张荫桓在日记中记述,容闳在哈特福德买了两套相邻的房子,其中一套是他们夫妇自住,另一套是送给威廉住。这些复杂的关系加上容闳对娘家人的态度,我猜测很有可能是在容闳的举荐下,陈兰彬同意聘请柏立担任中国驻美国公使馆的英文秘书。
1877年哈特福德的地图(局部)
从柏立的几任老板留下的日记来看,柏立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用英文誊写给美外交部的文书、去国会聆听有关中国政策的讨论并向公使汇报,以及一些外交场合的协助工作。柏立的工作情况,除了张荫桓(有39天的日记提到柏立)以外其他几个人都很少提及,比如陈兰彬《使美纪略》里只提到一次(随陈兰彬去白宫递交国书),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里只提到两次。尽管张荫桓多次在日记中提到柏立,但也多数是一句话代过,比如请其他使节柏立作陪、陪同张荫桓出席政府公宴、代张荫桓写英文函件、送张荫桓去白宫等等。柏立当时住在华盛顿特区K街NW的1705号,和中国使馆离得不远,张荫桓经常“随到柏立寓”。尽管可用的资料不多,但还是大体可以侧写出张荫桓眼中的柏立形象。柏立不喜欢吃中餐:光绪十二年五月初四日(1886年6月5日)张荫桓“晚约日本公使九鬼、前日斯巴弥亚公使科士达、本署洋员柏立宴会中华食品,二客皆欢,惟柏立甚以为苦。”柏立会奉承张荫桓: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87年2月11日)柏立去参议院旁听“洛士丙冷案”(“洛士丙冷”及Rock Springs音译,此案系1885年9月2日发生在怀俄明州石泉煤矿的白人矿工虐杀华人矿工案,有28人死亡,15人重伤,是美国排华期间的重案。)赔偿一事,大多数议员认为应该向死伤华人赔偿,同时“柏立又言近日美人皆有加敬中国之意,非复从前狂悖,颇归美余之耐烦应酬”,这话说到张荫桓心坎里了,他在日记中说自己“忝持使节,自以邦交为重”。而且主要的中国节日,柏立也不忘给张荫桓送礼,比如光绪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1888年2月11日)“柏立以英制磁瓶馈岁,取华语平安之意。”但有几件事让张荫桓对柏立的信任度下降。张荫桓的牙不好,柏立给他推荐了一位牙医,尽管“颇精细,器具亦良”,但“试以药,齿痛仍尔。”当然这个应该怪不到柏立,张荫桓的牙病已经很多年了,怎么可能用一次药就立竿见影。但张荫桓并不了解西医,他第一反应就是柏立推荐的不行。还有一次张荫桓去白宫“赴总统宴,不带翻译”,按张荫桓的说法是柏立曾经跟他说过前任郑藻如参加这种宴会的时候都是“伊送至宫门,属门者指明道路即返”,到张荫桓这里就变成了不再交代门者指明道路了,当张荫桓立刻指出这点时,柏立“愧悚,坚请随往,余却之,柏立益惭”,然后柏立又向负责接待的布朗说让张荫桓带个仆人进去“以代问答”,也被张荫桓拒绝了。更重要的是后来张荫桓发现所有的客人都是单独来的,没人带翻译或仆人,觉得“幸不为所诳”,这让张荫桓更不信任这位下属了。此外,张荫桓还觉得柏立的工作态度不认真。使馆的律师科士达总是第一时间把重要的信息传达给张荫桓,哪怕是很晚或是度假期间,“视柏立之急思携家避暑,用意自别”。还有一次张荫桓要在新年前宴请其他几位驻美公使,“柏立以公宴分两日,后请者不怿,未请之公使亦不怿,殆不亮客多不能并坐,而各国驻使无甚往还,又岂能遍约之乎?今春德使以德王生日宴客,亦未遍邀驻使,是岂余独矫异哉?叩以不怿者为谁,柏立又不能指出,是其师心自用,总以不预陪外部,为此妄言耳。”这都让张荫桓很生气,甚至在日记中写道:“洋员难共处,不悟前任何以耐之也。”对于张荫桓的不满,柏立应该也有所察觉,就在张即将卸任回国,新使崔国因将要到来的时候,柏立“虑新使不予蝉联,来函求荐,委婉之甚。”反正张荫桓要回国了,也没必要当那个砸人饭碗的坏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柏立的继任老板崔国因是个尚俭的人,他在日记里经常吐槽辖下三个使馆的各种浪费,对于“洋员柏立病重,久不到馆盖半年矣”的事情当然无法容忍,他当即决定“当与律师商酌设法裁之。”到了光绪十五年年底,崔国因终于下定辞退柏立的决心,他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十二月。与代办蔡函商辞退洋员柏立以为宜,彼此和平计议以全初终为合体,给以考语字据,俾其为转示于人之用,若以洋例,须先三个月告知,则与妥商办法或再留一年云。(崔国)因查雇用洋员每受其挟制,秘之德里安尤为荒唐。(崔国)因至此已久,柏立尚未来见,闻诸参赞盖久未到署矣。”此后崔国因在日记再未提起过柏立,想来当年十二月一定是把他辞退了。
柏立比他的好几任老板都活得长(陈兰彬1895年病逝、郑藻如1894年病逝、张荫桓1900年被杀、崔国因死亡时间不祥),一直到了民国元年才病逝,最后葬在华盛顿特区的橡树山墓园(the Oak Hill Cemetery)的218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