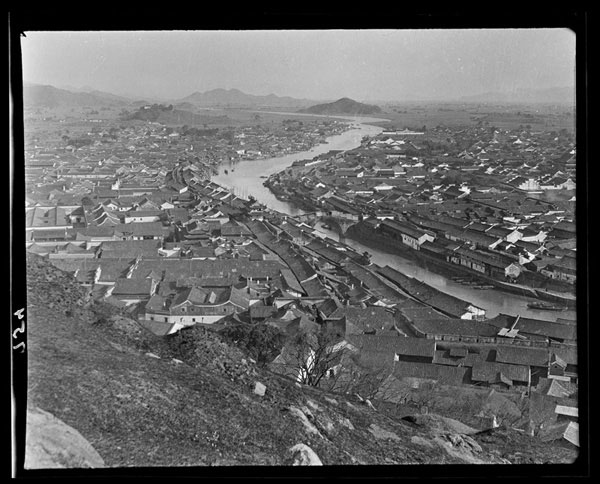照相机越来越小,越来越普及。自从换了带800万像素摄像头的手机之后,我已经很少摸单反了。随着微博的流行,无论老少,不管水平高低,人们都喜欢对着感兴趣的东西举起相机(手机),因为摄影术最基本的功能就是记录和传播。丰富且传播广泛的影像,拓宽了我们认识世界的眼界。可是在摄影术被发明之前,不同的文明之间只能通过文字和图画来相互了解。
1792-1794年,英王乔治三世派了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值乾隆盛世,使团中的多位成员在回到英国后都发行了见闻录,尽管各人对史实的描述大抵相同,但还是有些细节存在争议,唯一没有争议的就是使团绘图员(还不是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绘制的图画。先说说使团的大体行程是在白河河口沿水路到通州,再到北京城,穿城而过前往圆明园,把体积巨大和较精密的礼物卸下后,主要的几位成员前往热河觐见乾隆,从热河回京后仍然走水路,到杭州后一部分成员在舟山乘他们的帆船前往广州,马戛尔尼和部分团员走水路再走陆路再走水路,一路向西南最后到广州,两对人马在广州汇合后回国。其中前往热河觐见乾隆和从杭州走陆路往广州这两段重要的行程亚历山大都没有被允许同行,但是他仍然根据同伴的描述,用画笔记录下了这两段路程上的精彩瞬间,同其他经历过的场景一样,画了很多素描。他回国后又根据这些素描画了大量水彩画和油画。
使团成员所出版的见闻录里也多收录他的画作,其中最重要的共有三部,第一部是马戛尔尼私人秘书、使团副使斯当东1797年出版的《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An Authentic Account of an Embassy from King of Great Britain to the Emperor of China)。这一版本共3册,第一、二册是文字,第三册是大开本(43.5×58cm)的铜版画册,共收录44图,其中3幅动植物图,如交趾支那的霸王树及其叶子上的昆虫、爪哇的凤冠火背鹇和鸬鹚;11幅地图及海岸线,如舟山群岛、山东搬到和澳门等,特别是第一幅地图是使团往返的路线图,并详细标注了每个锚点的日期和水深,地图尺寸巨大,展开后的尺寸99×64.5cm;5幅剖面图,如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古北口长城、热河小布达拉宫、运河水闸、水车等;25幅中国的风俗人物,均出自亚历山大之手。这套书再版多次,但是再没有做过大开本的画册,因此这一版本现在的市场价值也很高。第二部是亚历山大自己出版的,这些描绘中国的铜版画是散页形式,共12辑,每辑4幅,从1797年7月直到1804年11月出完,最后在1805年发行了合订本,书名为《中国服饰》(The Costume of China),这48幅铜版画都经过手工上色。第三部是1814年英国发行的一套4本的“图鉴”画册,其中一册是亚历山大绘制的《中国人的服饰和风俗图鉴》(Picq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另三本分别是奥地利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服饰与习俗图鉴”。这本书中收录手工上色的铜版画50幅,与1805年出版的《中国服饰》不同。
最近有幸经手一套《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虽然俩面的图画在网上、书上打都见过,但是细细摸索这些精美的原作,那份快感无可言述。特别是里面第一幅地图资料性很强。因为关于使团的行程,国内只有费振东先生的译著《英国人眼中的大清王朝》值得参考,费先生做了很多考证,但有些地名还是错译,甚至只是音译,有了这张地图作参考,很多问题都会解决了。
最后看看马戛尔尼在热河见乾隆那幅铜版画的细节吧。
 《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书中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的铜版画
《大英国王派遣至中国皇帝之大使的真实报告》书中马戛尔尼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的铜版画
 乾隆皇帝的局部
乾隆皇帝的局部
 戴羽毛帽子的是马戛尔尼,他旁边可能是翻译柏伦白,后面拉着斗篷的是小斯当东
戴羽毛帽子的是马戛尔尼,他旁边可能是翻译柏伦白,后面拉着斗篷的是小斯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