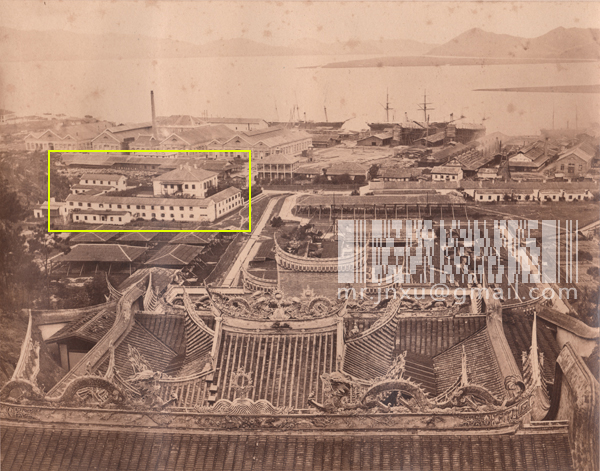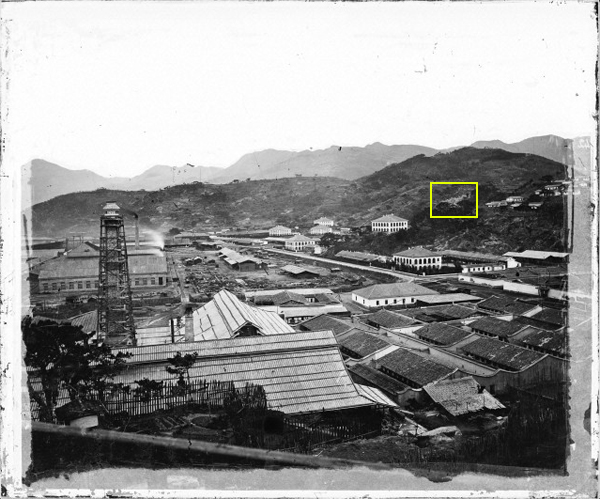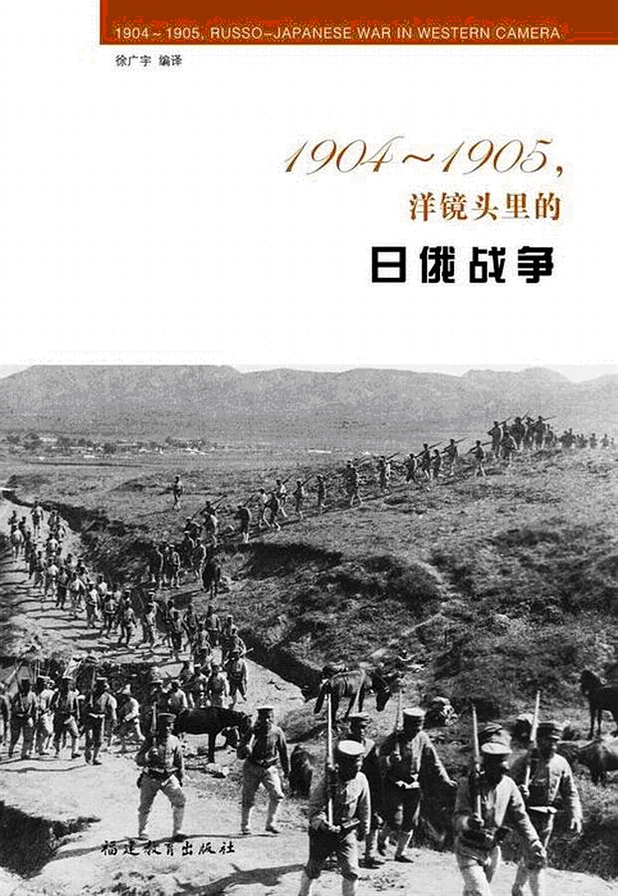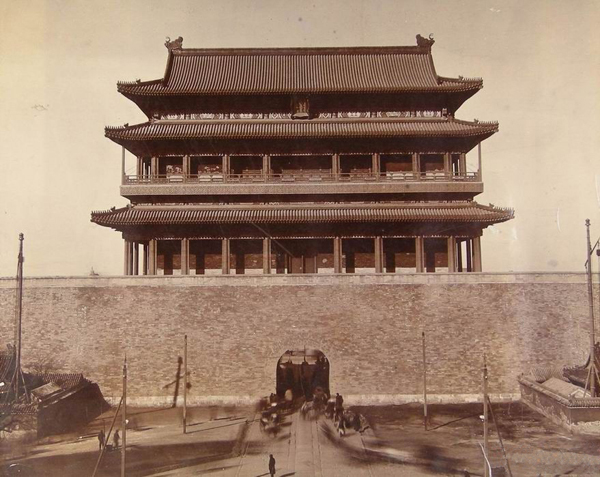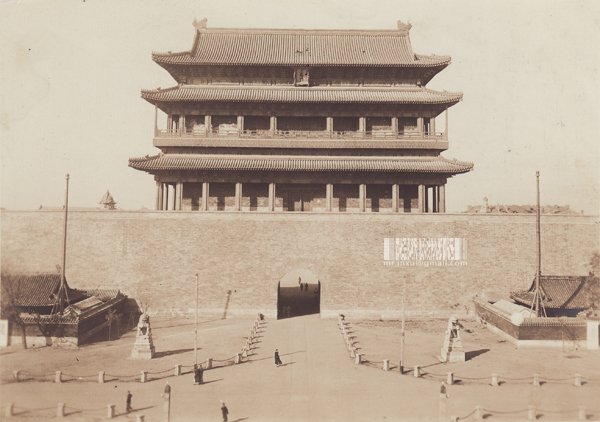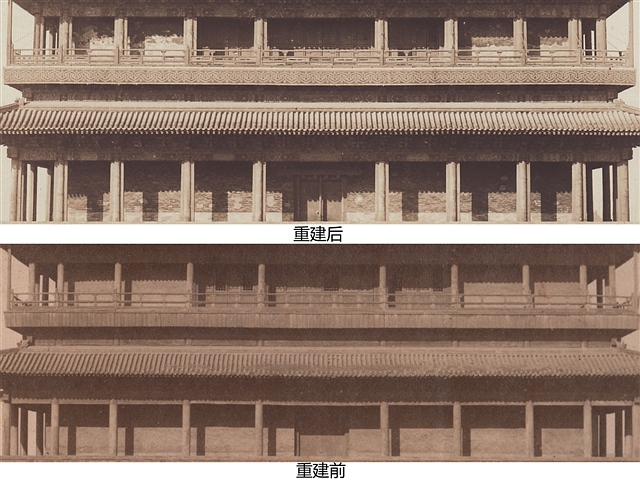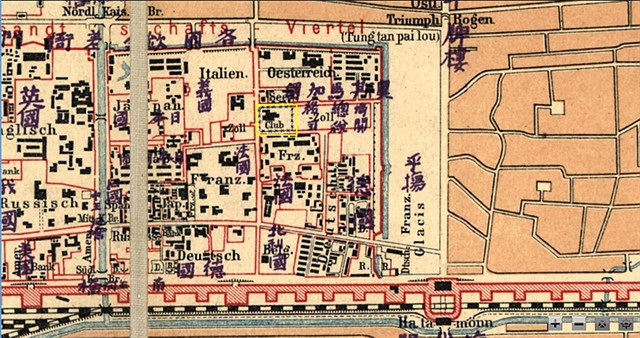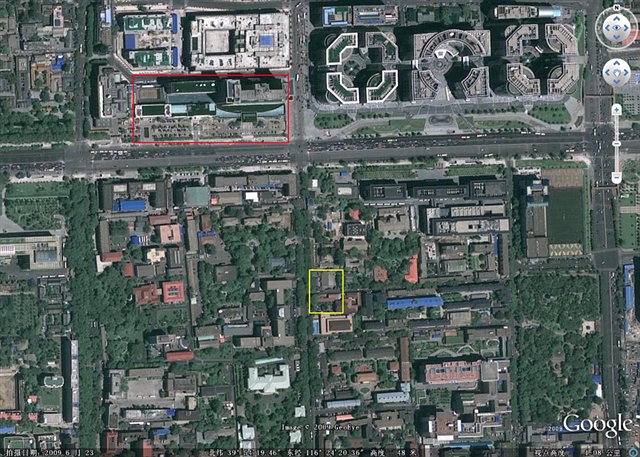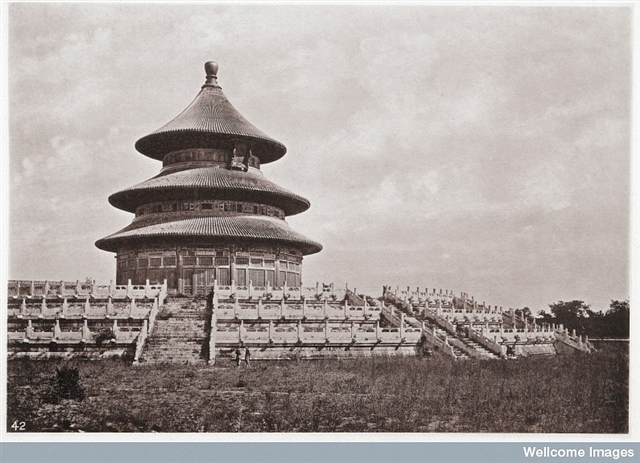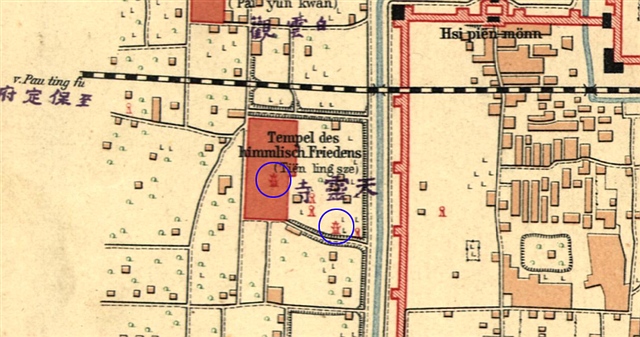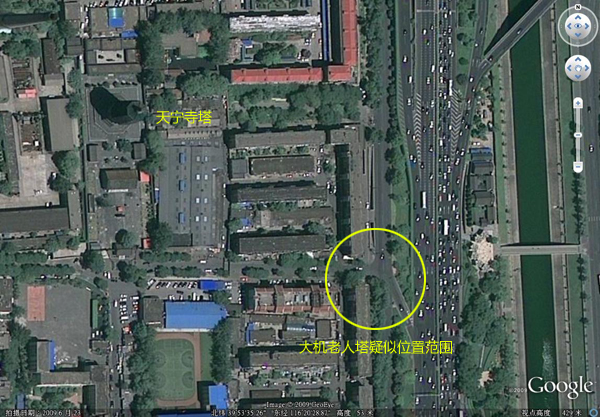福建教育出版社的新书出来了:《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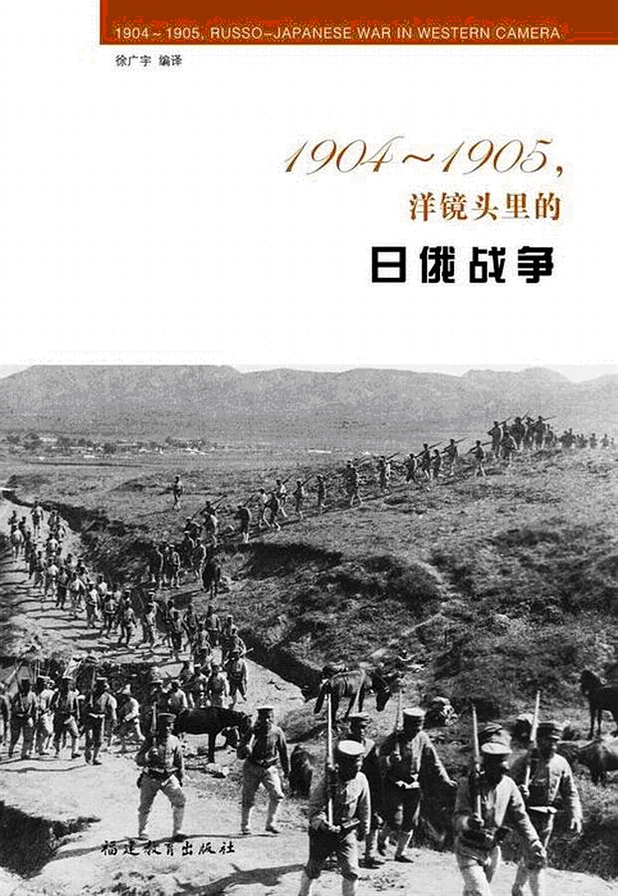
内容简介:
本书源自1905年美国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出版的一套98张日俄战争的立体照片,多数照片都有英文的说明,编译者对其进行了整理、翻译。借这些外国摄影师的镜头再现了一百多年前,以中国东北为战场,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地盘的那场不义战争的一个侧面,可看到日军在这场战争中的军备装置、官兵士气、战场火拼、日胜俄败,中国人民惨遭涂炭等真切的战争场面,令今人反思良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杨天石先生作序,摘录如下: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套一百多年前在国外出版的照片集,.原名《日俄战争专辑》,反映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中国东北等地的权益,在我国的领土上所进行的一场肮脏战争。但是,它并未反映战争的全过程,而是选取其中具有关键意义的旅顺攻防战作为焦点。旅顺攻防是日俄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海陆鏖战,长达5个多月,日军参战13万6千人,死伤6万2千人;俄军伤亡2万1千人,被俘3万3千人。其结果是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战胜了老大的沙俄帝国主义。这场战争不仅世界瞩目,中国人普遍关心,并且给了中国的革命党人、立宪党人和清朝统治集团以巨大影响。《日俄战争专辑》共收照片98帧,都是英、美和日、俄的随军记者们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现场拍摄的,它们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有许多是其他文字史学所无法反映的。今天看来,不仅可以增加我们对那场战争的具体认识,而且同时会带给我们惊心动魄的感受。
收录的部分立体照片和文字:

拍摄照片的位置是停泊于旅顺港内的阿莫尔号(Amur)甲板上。佩列斯韦特号(Peresviet)整装待发,准备加入港口外的一个预备舰队。
自1904年2月战争爆发,佩列斯韦特号参与了数场艰难的战斗,舰载的大炮对日军的炮火给予了强有力的还击。该舰装备有大炮七十多门,多数为速射炮,并有六个鱼雷发射管。这些大炮的射程达三英里以上。由于该舰水线以上有近四十英尺的高度,她很容易成为敌人排炮攻击的目标。这艘船建造于1898年,她的引擎能提供14500马力的动力,使其能轻易地达到每小时18节的航速。
约有六万名官兵服役于俄国海军的各个舰队,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叔父亚历克斯大公(Grand Duke Alexis)担任总司令。极负盛名的“海洋哥萨克”马卡诺夫将军(Admiral Makaroff)直接指挥对日作战的舰队,直至1904年4月13日,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Petropavlosk)悲剧性的沉没为止——这艘船触了日本人布下的水雷(关于所触水雷属日方还是俄方,史上并没有定论,在此依照原文翻译——译者注),沉没于港口入口处,马卡诺夫和全体船员葬身鱼腹。之后斯蒂洛夫将军(Admiral Skrydloff)接掌了舰队的指挥权。

椅子山在旅顺西北,山上筑有堡垒。旅顺周围的山峦都比较荒凉,只有山谷间的土地适宜耕种,照片中日军士兵远处能看到当地中国人的村庄和成片的田地。在这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而中国政府没有参与的战争中,很多无辜的中国百姓被牵连其中,生命和财产都遭受到损失。

旅顺城和海港在照片拍摄方向背后一英里以外。这里位于两个强悍的炮台之间的岩脊之上,炮台被加固,以防日本人的进攻。沿着山脊筑满了用沙袋和木板修建的工事,就像我们看到的这样,用来为狙击手提供保护。这名颇有男子气,被称做哈留申(Khariton)的士兵,与她的丈夫,一名从西伯利亚征招来的列兵一起来到旅顺。这里没有妇女的位置,日本人的进攻像拍打岩岸的海浪一样,一次又一次永不停歇。但是既然她的丈夫在这里,这就是她的位置,克里缇娜(Kharitina),这是她真正的名字,穿上了军装,跟随她的丈夫来到这里,她要求一支属于她的步枪,并发誓用它来捍卫荣誉。多么荒谬而不可思议!由于枪支缺乏,这位自命的狙击手转而充当护士、女招待和缝糿工——在所有这些简单而卑微的工作中她全心全意地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同时契而不舍地要求一支枪。她一直坚持。一天她的丈夫受重伤住进了医院,往返于丈夫的病床和阵地之间,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急切地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被她的激情所感动,或是抵不住她不断的请求,在她无私地奉献了三个月之后,他们终于把武器交到了那双纤细的手里。带着相机来到这里的俄国摄影师说:“她刚刚从医院匆忙地看望了她的丈夫回来,他好些了。在这张照片被拍摄的两个小时后,一枚日军的炮弹袭击了这里,她当场死亡。”

我们现在位于旅顺俄军防线的最前沿,松树山炮台就在十几米以外。
这里的气氛冷漠得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作为一名士兵对这种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恐怖场景必须习以为常。
仅仅几个小时以前,日军——现在这些堆积在战壕里的尸体,对这个炮台发起了一次冲锋。他们从那道护墙前面较远的地方攻过来。俄国人从墙上的窥孔里注视着他们的行动(在画面右边的那些人的肩膀上方我们能看到一些那样的孔),炮台的全部火力都对准了他们,隐藏在这堵墙后面的步枪迎面送去雨点般子弹。超过半数的日军倒在了那堵墙之前荒芜不平的山坡上,余下的人纷纷爬过栅栏,孤注一掷地想要攻下这片阵地。这里一度变成了地狱。子弹让位于刺刀,用于可怕的近身搏杀。
现在俄国人已经把他们的伤员转运到最近的战地医院,他们修整了护墙,垒起了更多的沙袋。对日本人来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只是掩埋好阵亡者的遗体。没有俘虏,没有伤员,在这次战斗中,所有人都倒在了胜利者的脚下。然而日军其他的部队却可能在任何时间,再次发起一次这样的攻击。
 秀山堂残迹
秀山堂残迹 秀山堂残迹
秀山堂残迹 木斋图书馆,从二层的窗户还能看到坍塌的穹顶
木斋图书馆,从二层的窗户还能看到坍塌的穹顶 木斋图书馆原貌,图片来自南开大学网站
木斋图书馆原貌,图片来自南开大学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