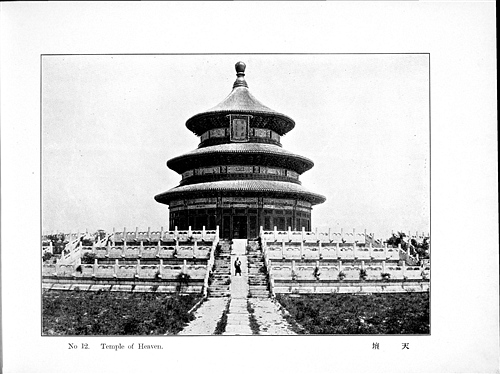最近整理老照片发现两张照片中的乞丐竟然是一个人!
图片来自美国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1901年发行的《China》立体照片集
照片来自1900年左右某位游历中国的德国船长收藏的相册
很明显,这两张照片都摄于上海龙华寺,而且也都是同一个乞丐。旧时中国,(大)寺庙前多乞丐(其实现在也差不多),能烧香拜佛的多数还算能也愿意施舍的。能被两位不同的摄影师在不同的时间拍摄下,想来这个乞丐也不就是在此地很出名,或者衣衫褴褛的程度很高,能引起猎奇的外国摄影师的关注,再有一种可能就是此乞丐会围着外国人讨钱……什么原因被留在影像里已不可考,但这个老乞丐的形象却巧合的能流传100多年甚至还将继续流传下去,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