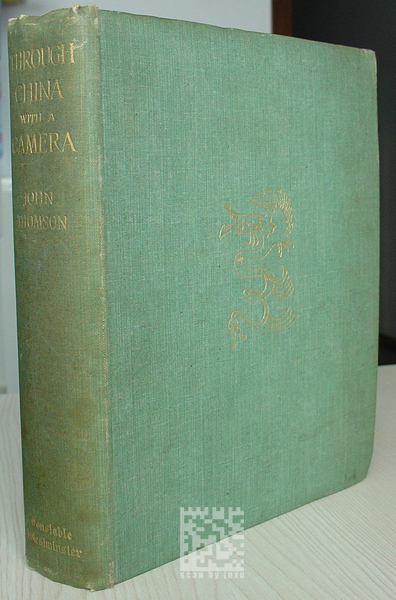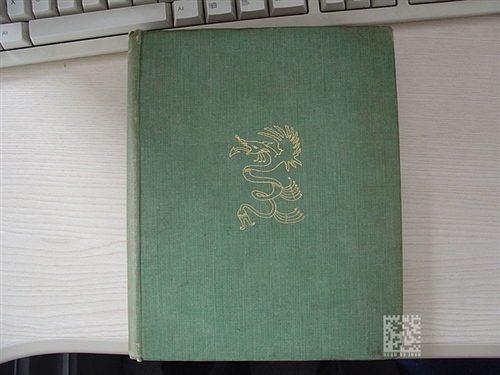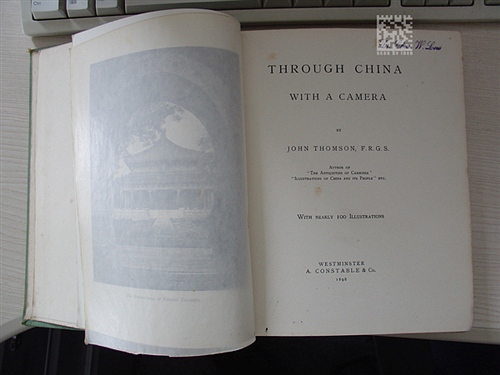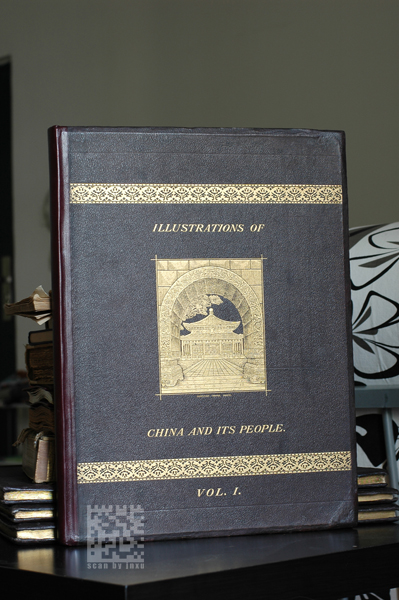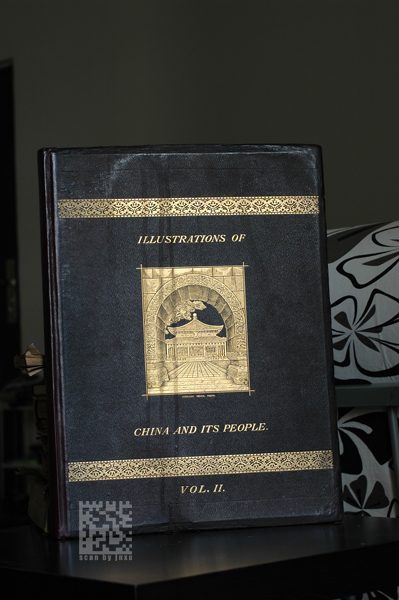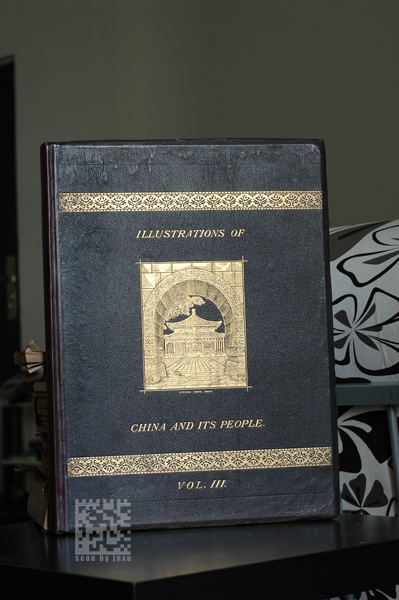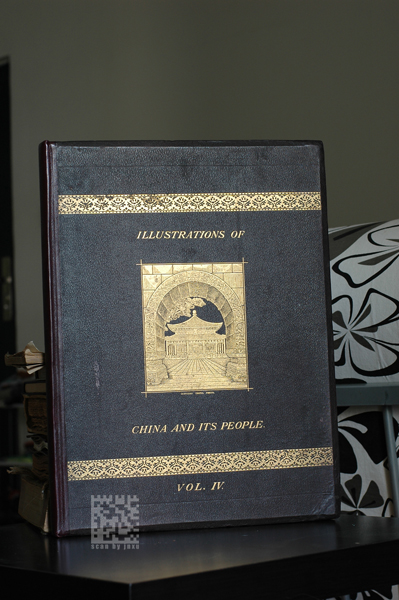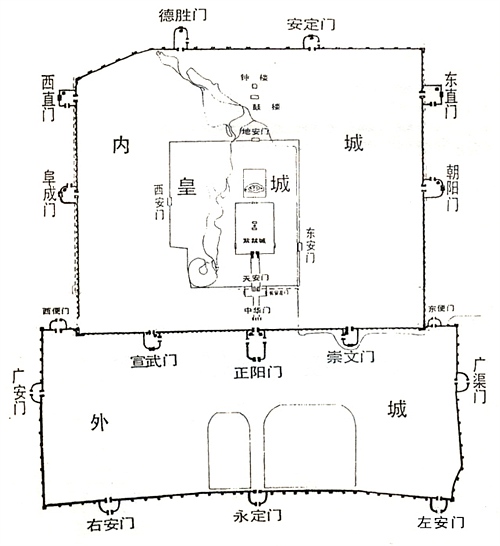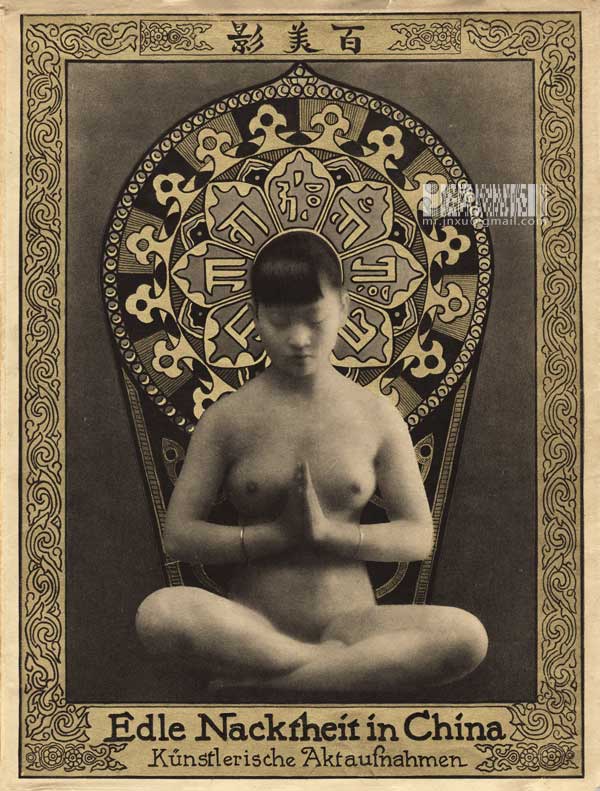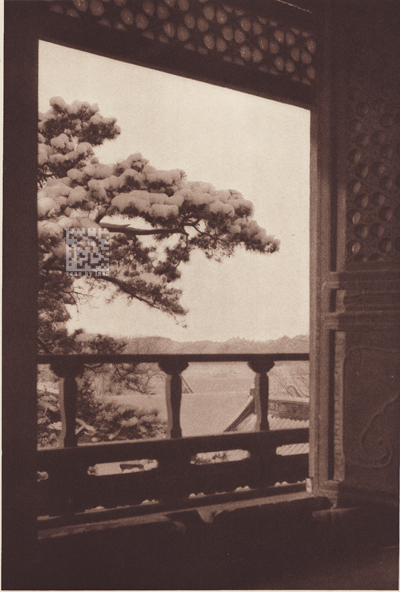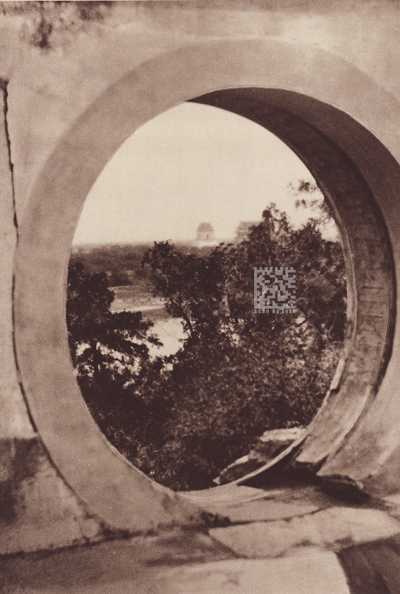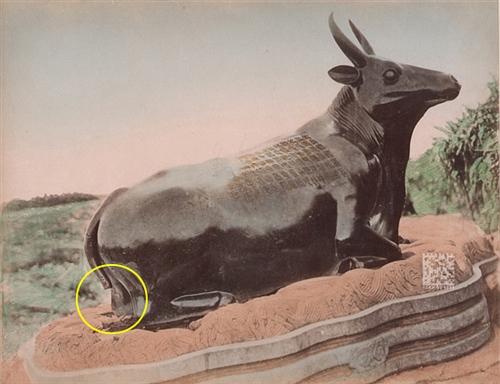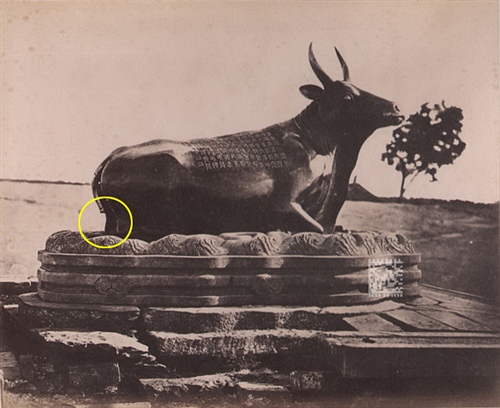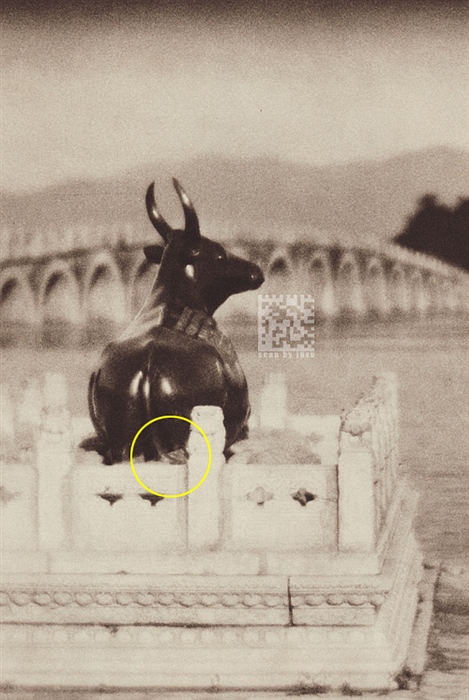这篇文字是为原计划最近一次拍卖会准备的(仰仗朋友们帮忙,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攒了一场拍卖会的东西,在病假中考证、拍照、写字),无奈遭遇延期,但字不能白码,放到blog里也算一份留存。
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肖像
1839年,法国政府公布了以“达盖尔”命名的银版照相法,从此摄影术诞生。银版照相法是将一面光滑的铜板镀银后,在碘溶液里浸泡使之感光化(产生碘化银),然后放在“照相机”中进行曝光,之后用汞蒸汽熏,使之显影,最后用海波溶液洗去未曝光的银盐使之定影。摄影术的诞生在科学和艺术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改变了人们的生活。“逼真”这一特征使“记录”成为摄影术最重要的作用,而这种“记录”的最普遍应用就是拍摄肖像,以保留人们的容颜。
关于“肖像”的定义,美国著名肖像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1856-1925)幽默地说:“肖像就是看起来像但总有哪里不对劲的画像。”美国画家、艺术评论家莫里斯•格罗瑟(Maurice Grosser,1903-1986)说:“肖像是4-8英尺外再现的一个不用付费摆拍的人。”艺术史学家理查德•布里连特(Richard Brilliant,b.1929)认为肖像应该回答被摄主体的问题:“我看上去是什么样子?”“我是什么样子?”“我是谁?”摄影术传入中国之初,多数中国人可能都没法回答上面这三个问题。能主动去拍摄肖像的人是极少数,他们属于富裕而且思想相对开明的阶层,比如官员、富商等等,就算他们有主动的意识去思考上述三个问题,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怎样将他们对自己的认识通过眼前这种新鲜的方式表达出来。因此诠释这三个问题的责任完全落到了摄影师的身上,由他们来决定被拍摄对象“看上去是什么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子”、“是什么人”。肖像也是为数不多的需要第三方,即观看者参与的艺术形式。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层次,会对相同的信息产生不同的解读,这也是肖像的魅力之一。
1844年,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 Itier,1802-1877)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乘坐西来纳号战舰来华,他于10月抵达澳门,然后换乘阿基米德号船到达黄埔港。他在中国期间参加了中法贸易协定的签字,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了两国的代表——拉萼尼和中国总督耆英。他还拍下了码头和城市的实况,拍摄了潘仕成的肖像及其家庭的照片。埃及尔成为第一个将摄影术带到中国的人,第一个拍摄中国人肖像的人,这些银版照片至今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耆英、潘仕成的家人、街头的苦力应该都没有想过他们留下的这些影像对后人的意义。
 于勒1844年在广州街头拍摄的苦力
于勒1844年在广州街头拍摄的苦力
 于勒1844年拍摄的广州官员
于勒1844年拍摄的广州官员
 于勒1844年拍摄的潘仕成家人
于勒1844年拍摄的潘仕成家人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更多的中国沿海城市成为通商口岸,大批形形色色的西方人,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来到中国,摄影术也随之迅速在这些口岸普及。不断传回西方国家的文字、版画和照片使得他们对神秘东方的兴趣更加浓厚,这也促使从香港到广州再到上海,在这些沿海城市不断出现的职业摄影师和照相馆更加乐于拍摄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
关于如何拍摄肖像,怎样让被摄者摆造型,西方有一整套从绘画继承而来的理论,在摄影术发明之后,出现了很多此类的指导手册,这些手册基本上都遵循着画家提香(Tiziano Vecellio, 1490-1576)、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等人提出的肖像画艺术规范:眼睛应直视相机斜上方,凝视那里的某个物体,决不要把目光放在设备上……手应保持松弛,轻轻放在膝上,不要太高也不要太低,或一只手放在桌子上,另一只手拿本书或其他东西……这种规范是早期肖像摄影师,特别是西方摄影师严格遵循的,如图一,威廉•普莱尔•弗洛伊德(William Pryor Floyd)拍摄的两名满清官员目光交错,视线都落在照相机旁的某个点,一只手放在茶几上,另一只手轻轻地方在膝上;同样是弗洛伊德拍摄的图二,两个汉族妇女也同样将目光凝聚到照相机的旁边,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另一只手捏着手帕放在膝上。尽管这两位妇女在拍摄这张合影的时候没有主动去思考那三个问题,但是她们的发型、衣着、首饰、状态以及摄影师的精巧摆布都向我们诉说着这两个人的身份和故事。首先,两位坐着的妇女从服饰、发型和裹脚的习惯来看都是广州、香港一带的汉族。早期能去照相馆拍摄肖像照片的女性无非两类,富人的家眷或风尘女子。两位妇女没有摆出招揽生意的撩人姿态,而且茶几上那十本《古文评注》说明她们不是风尘女子。她们穿着相似的衣服,戴着相似的绞纹手镯,两人可能是共事一夫。古人以左为大,坐在左边的这位虽然出身稍微差些(手粗大,肯定经常劳动),但已经为这家人续了香火,应该为大;坐在右边的这位身材娇小些,双脚必须踩着脚踏,手也纤细很多,还带着戒指,说明在家里更受宠爱,为妾。边上的孩子懵懵懂懂,站在母亲身边看着照相机,眼神里充满好奇。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有些人能够接受摄影师的摆布,但有些人不能。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人的面目怎么能留有阴影或者目光旁视?比如图三曾纪泽肖像。曾纪泽虽然长期担任大清朝的驻外使节,思想开放,但是作为曾国藩的长子,性格耿直的他不可能完全听从摄影师的摆布,在这张照片中虽然他也是一只手放在茶几上,一只手放在膝上,但是他表情严肃的正视照相机,脸上没有留下一丝阴影。同样身居高位的李鸿章长期和外国人打交道,经常有机会拍照,因此在观念方面更开放些,他就可以将头偏向一侧,不正视照相机,只是双手的摆放略显沉闷,保持着中国传统肖像画的姿态,如图四。晚清著名外交官伍廷芳的这张肖像是在法国拍摄的,似乎完全是入乡随俗,姿态很放松,并非“正襟危坐”,而且三位外国人环列于其身后,这是纯正的西方专业摄影师的风格。在不听从摄影师摆布的肖像作品中还有一类很有趣,比如图五中这位青楼女子的肖像。很明显,摄影师让她侧身对着照相机,一手扶茶几,一手攥着手帕自然下垂,目光也应该是随着身体的方向望着照相机的一侧,然而她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其他缘故,却在底片曝光的那一刻对着照相机偷偷瞧了一眼,嘴角还露出浅浅的微笑,透过照片似乎能看到她年轻的心。同样是青楼女子肖像的图六中六女子合影,虽然我们无法用现在的审美观来看待她们的形象,但这种“厚”施粉黛的装扮的确能说明当年的潮流。摄影术是舶来品,关于如何拍摄肖像也要向外国摄影师学习,但是一些摄影师的学习会根据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作变化,比如图七的妇女坐像,姿势就死板很多。
 图三
图三
 图四
图四
 图五
图五
 图六
图六
 图七
图七
如果说上述这类中国早期的室内肖像中,被摄者多少还有些主观意识的话,那另一类室内肖像可以说完全没有了被摄者的主观表达,完全是由摄影师来诠释和表达。19世纪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更为迫切,特别是在摄影术已经普及后,因此很多在中国的商业摄影师都会拍摄一些他们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记录迥异于西方伦理观和世界观的内容。他们雇请各行各业的中国人在摄影棚内再现他们平时的生活状态并记录下来。在上海开设照相馆的美国摄影师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擅长此道,而且视角相对客观。他在上海的开设的森泰照相馆从1860年代一直持续到1880年代,他拍摄了一些上海及其周边的风景,更多的时候他将镜头对准了中国的普通百姓,如街头卖零食的小贩、流动的小吃摊、人力车夫、囚犯、抽鸦片的人等等。在街头卖零食的小贩这张照片(图八)中,一名男子头戴旧毡帽,辫子盘在毡帽上,毡帽下似乎还别着一根烟签子,他衣衫褴褛,左臂挎筐,里面装着馓子和其他一些小零食,右手擎一把破伞,目光同样没有落到照相机上;裤腿高高的挽起,一双赤脚踩在稻草上(桑德斯经常会在他在摄影棚内构造的场景里铺上稻草,这是判断其作品的标志之一)。19世纪的上海多雨,且旧城内的公共道路状况不好,很泥泞,这些都可以从这个小贩的打扮看出来。这张照片还经过仔细地手工上色,甚至小贩腿上的污泥都做了还原,使他的形象更加真实。我们无法深究他所卖食品的卫生状况,不过这可能就是十九世纪部分上海底层百姓的形象。在桑德斯留下的室内肖像作品中,还有一对年轻的新人合影(图九)。新郎一副官员打扮,手拿一把折扇,看着年纪尚小,眼神中透着执著与镇定,似乎已经明白即将承担一个家庭的重任;新娘也是凤冠霞帔,几根珠帘从凤冠上垂下,遮挡住部分面庞,羞涩下难掩喜悦,作为观看者也能感受到他们的幸福。
 图八
图八
 图九
图九
除了在室内拍摄各类中国人肖像,一些摄影师还走上街头外拍。Burton F. Beers的《China, In Old Photographs 1860-1910》的封面曾选用了一张街头修鞋匠的肖像照片(图十)。这个年轻的鞋匠坐在路边,放下担子。左边的担子下面是个圆盒,上面是个方盒,用来装他的工具;右边的担子是个箩筐,挂着一块皮子,箩筐里面可能是用来补鞋的材料和用来展示他手艺的样品。不知道他把工具放在膝上是不是因为已经有了生意,还是应摄影师的要求摆出的姿势,两眼望着远处。细看他的两只鞋都打了补丁,这大概算是广告吧。透过照片中的细节,不用怀疑这个年轻人的真实身份,他一定是个真的修鞋匠。而有的照片中的人物可能仅仅是“群众演员”,对于他们在照片中扮演的职业并不熟悉,比如另一张模拟街头场景的照片,摄影师似乎是要拍摄一个小贩卖梨,旁边有独轮车通过的场景(图十一),里面的买卖双方和乘独轮车的人都好扮演,但两个成年人的重量可苦了这位非专业的车夫,从他痛苦的表情中能看出来他再坚持不了几秒钟了。
 图十
图十
 图十一
图十一
对于这些十九世纪的中国人肖像,无论是否摆拍,是否出于摄影师的客观表现,它们至少都记录了一份属于那个年代的真实。一百多年后我们重新解读和收藏这些影像,依然能够感受到摄影者的所见所想、被摄者的喜怒哀乐,感受文字描述不能带给我们的历史,这是从这些旧影像、老照片中升华出的价值。